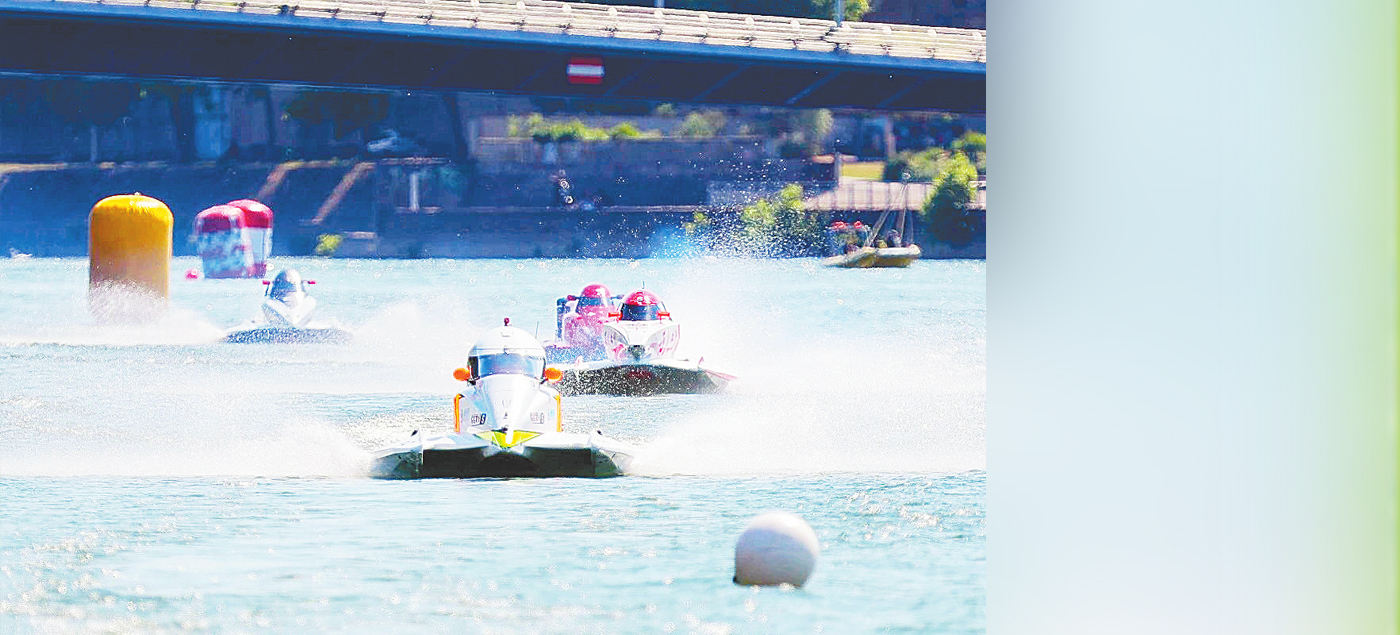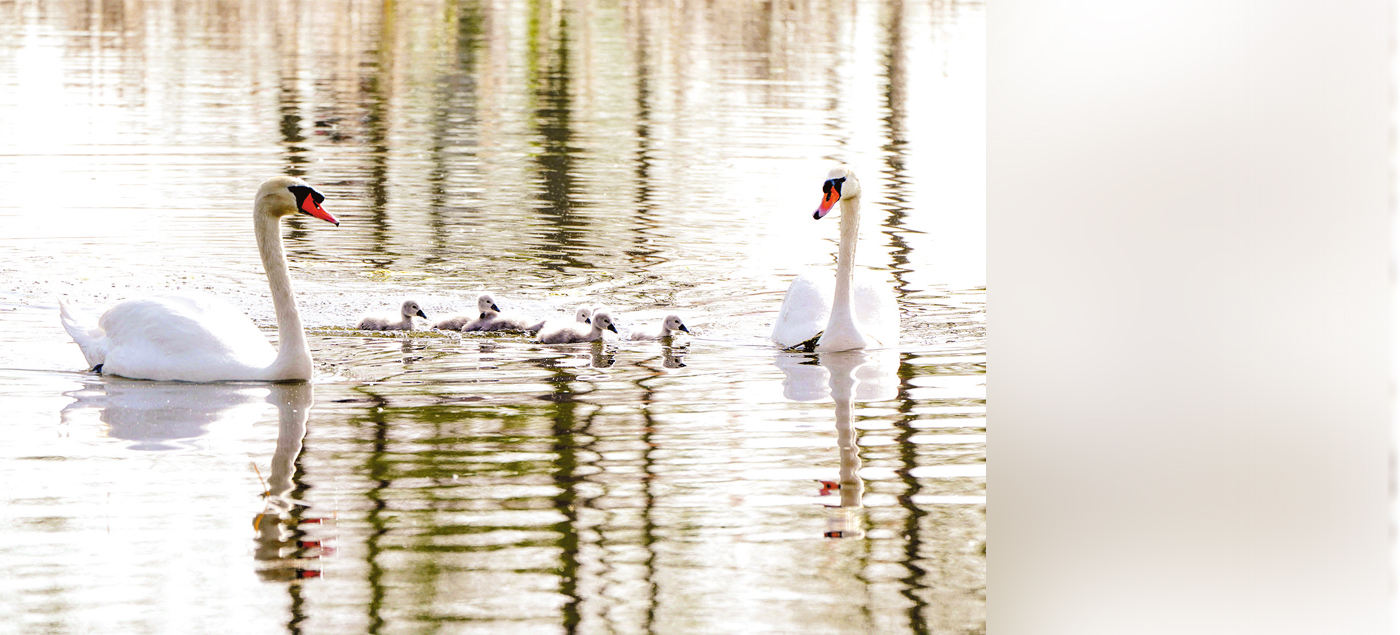只是喜欢 | 马

韩干一定是酒后挥毫,才画出如此昂扬的《照夜白图》。那已经不是一匹马,而是蓬勃向上的大唐。

▲韩干:《照夜白图》,唐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
如此神骏,谁看了不心潮澎湃呢?
哈尔斯也是喝了大酒,才在骑士的脸上,绘出天下最自信的微笑。
那是新贵崛起、自由奔跑的荷兰。

▲赵孟頫:《人骑图》,元,故宫博物院
而赵孟頫笔下的马,就沉默了许多。这幅《人骑图》就是这么稳当:不偏,不倚,不迎,不拒,不悲,不喜,自命不凡,含蓄内敛,引而不发……
作为元朝的文人,怎么画的出激昂呢?
他的《浴马图》,则在马放南山的太平外表下,隐藏了重重密码。
岸边洁身清傲的白马,河中同流合污的花马,洗完风中凌乱的灰马……
寄人篱下,哪有那么容易!

▲龚开:《骏骨图》,元,大阪市立美术馆
同时代的龚开,境遇凄惨,他画的《骏骨图》瘦骨嶙峋却仍是铮铮铁骨,让人过目难忘。

▲金农:《良马图》,清,佳士得2008春拍
到了金农的《良马图》,又自有一番气象。您看此马:劲如铁,势未发,有顾影自怜之意。
“世无伯乐,即遇其人,亦云暮矣!”
金农托古改制,另辟门径,开宗立派,终成一代大师。但其一生布衣之身,谁知其难,谁解其悲呢?
金农不是在画马,是在画自己。
任仁发则在画兄弟。他的《五王醉归图》,跑在最前面的白马即是“照夜白”。
唐玄宗兄弟五人,饮宴尽兴,大醉而归。玄宗已醉的不省人事,伏在马背上,贵为帝王,却不留一丝戒心。

▲康定斯基:《蓝骑士》,1903年,苏黎世布尔勒收藏展览馆
主动让位给小弟的兄长李宪,骑黑马紧跟其后,虽也醉眼迷离但时刻不忘照看好三弟:小子你可不能有闪失,李家就看你了!
最后面骑花马的老五身着红衣,也醉的趴在马背上。喝酒程度、着装颜色,都和玄宗保持一致!
莫说帝王之家,就是平民百姓,兄弟之间情深至此,怎一个羡慕了得!

▲约翰·马勒·科里尔:《马背上的Godiva夫人》,1898年,赫伯特美术馆和博物馆
2012年初,我坐在电影院里毫无征兆的开始抽泣,控制不住的抽泣。
那天上映的是斯皮尔伯格的《战马》。
打动我的显然不是马,而是在那么残酷的战争中,在所有人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痛之后,围绕一匹马而展露出来的人性的善。
那善意的光芒如此闪耀,瞬间击穿人心,不能自已。
大师就是大师,不管直面了多少不堪,仍然为我们保持着光亮,保持着温暖,那是人类这可怜的生物生存繁衍的原始力量。
如今,我们的生活早已远离了马,但愿我们的身心,都能永远奔腾不息。
作此文想到了这些画
或者是看了这些画作了此文:
赵孟頫:《人骑图》,元,故宫博物院
赵孟頫:《浴马图》,元,故宫博物院
韩干:《照夜白图》,唐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
李公麟:《五马图》,北宋,东京国立博物馆
龚开:《骏骨图》,元,大阪市立美术馆
高更:《沙滩上的骑马者》,1902年,法国
钱选:《贵妃上马图》,元,美国弗利尔美术馆
康定斯基:《蓝骑士》,1903年,苏黎世布尔勒收藏展览馆
任仁发:《五王醉归图》,元,上海龙美术馆
赵佶: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,北宋,辽宁省博物馆
金农:《良马图》,清,佳士得2008春拍
华金·索罗拉:《浴马》,1909年马德里索罗拉博物馆
雅克·洛朗阿佳森:《阿拉伯人带领穿过沙漠》,1810年,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
约翰·马勒·科里尔:《马背上的Godiva夫人》,1898年,赫伯特美术馆和博物馆
佚名:《洗马图》,明,辽宁省博物馆
乔治·斯塔布斯:《母马与马驹》,1760年,伦敦泰特画廊
法国弗朗索瓦一世骑马图,1540年,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
乔治·斯塔布斯:《马与狮子》,1770年,利物浦华尔克美术馆
席里柯:《埃普瑟姆的赛马》,1821年,巴黎卢浮宫
拉斐尔:《圣乔治屠龙》,1505年,巴黎卢浮宫
毕加索:《牵马少年》,1905年,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
保罗•高更:《白马》,1898年,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
亚克.路易.大卫:《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》,1800年,法国马尔梅松城堡
燕文贵:《扬鞭催马送粮忙图全卷》,北宋,大都会艺术博物馆
埃德加·德加:《草地上的马》,1871年,美国国家艺术馆
可能比较搭的音乐
老约翰·施特劳斯: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
普罗科菲耶夫:《第三号钢琴协奏曲》





 联系记者
联系记者